本文共12340字,閱讀時間約為23分鐘。
20多年來,中國作為體育大國,在花滑女單項目的獎牌數是:零。
20多年來,體育界、冰迷都渴望着有人能夠打破這個尷尬的數字。
2019年時,一個12歲的小女孩橫空出世,一舉獲得全國花滑成人組冠軍,從此,這個叫「安香怡」的女孩成了「全村的希望」。

安香怡有最好的訓練條件嗎?答案是沒有。有最好的團隊嗎?不好說。人們現在唯一能肯定的是,她有一個「瘋狂的」、一點也不打算後退的媽媽張愛君。
撰文:武奮豐
編輯:杜強
攝影:李松鼠
53歲的張愛君把目光投向冰場。
哧哧——哧——冰鞋滑過冰面,女兒妮妮像小鳥般飛起。她本該在空中完成旋轉後穩穩落冰,但她摔倒了,瘦薄的背影屈身而跪,拳頭焦躁地捶向冰面。
張愛君神情嚴肅,沉默着。片刻後,當女兒再次從面前滑過時,她緊繃着臉喊道:「勾手不夠周,內點也摔,不能證明你自己,你得證明你自己!」凌厲的聲音迴蕩在冰場上空。她所說的證明,意思是讓妮妮照着奧運會的標準要求自己:她要將女兒塑造成世界頂級的花滑運動員。
冰場上的其他人——手執教棍、表情鬆弛的教練,興致勃勃學習滑行的小孩,偶爾經過的開着清冰車的大爺,對這對母女堪稱極致的訓練早已見怪不怪,但熟悉冰上運動的人知道,張愛君的想法絕非易事。
花滑界有一種說法:世間最難培養的是飛行員,花滑運動員次之,更何況目標是世界頂級。然而對張愛君來說,花滑的困難是一種說法,她認同,但不服氣,認定的事就一定要走到底。
於是,在全世界的媽媽恨不得給嬰兒最安寧的懷抱時,2007年,張愛君依照一套美國嬰兒體能訓練課程,抱着兩個月大的妮妮練習轉圈。先順時針轉十圈,再逆時針轉十圈,至於這種訓練能起到的效果,張愛君說,將來坐十遍過山車頭都不會暈。
在整個嬰兒期,妮妮每天都會接受來自張愛君的不同訓練,包括在地上爬行、頭朝下轉圈。再長大一點後,張愛君讓妮妮站進北京的冬天經受七級大風。過路人好奇:這大風天怎麼有兩個小孩站在外面不回家?「有一個是我們家妮妮,還有一個是農民工的孩子凍着呢!」伴隨一陣爽朗的笑聲,張愛君說道。這是她把女兒推向世界頂級的第一步。
在張愛君看來,女兒未來會進入國際賽場,和俄羅斯人、日本人對決,因此必須擁有強健的體魄,「我們做的事和打仗是一樣的」。體能訓練的成效令張愛君滿足,在不斷加速的情況下,7歲時的妮妮可以跑完4000米,這一幕曾把田徑場周圍的人看呆了。
但凡一個人抱定了如此決心,她大概率不會遭到辜負。到了2019年,年僅12歲的妮妮參加了全國錦標賽,成人組,並如願成為賽事歷史上最年輕的冠軍。於是在陳露之後,中國花滑又擁有了一個可以衝擊世界級獎牌的天才少女,冰迷們也立刻被這個叫安香怡(妮妮本名)的小姑娘迷住了,建了後援會、在貼吧中緊跟她的動向,也少不了為她們母女感到憂心——中國在花滑女單項目的獎牌荒已經持續了20多年,最好成績是李子君2013年世錦賽上的第7名。
不光中國,實際上全世界的花滑女單選手都活在俄羅斯鐵血女王「面姐」(Eteri Tutberidze)的影子底下,以至於人們說,花滑女單只有兩個隊,面姐隊、非面姐隊。面姐的姑娘們人高馬大、力量驚人,13歲就能跳四周,得分比男選手還要高,上屆冬奧會包攬金銀牌,一度逼得國際滑聯商討修改規則。
這就是13歲的安香怡將要面對的。她瘦瘦小小的,還很稚嫩,但已經背負起了在花滑賽場升起一面國旗的熱烈期待。
關心她的人不禁會問,安香怡有最好的訓練條件嗎?答案是沒有。有最好的團隊嗎?不好說。人們現在唯一能肯定的是,她有一個「瘋狂的」、一點兒也不打算後退的媽媽張愛君。
對張愛君而言,讓女兒學花滑是水到渠成的事,不僅因為丈夫安龍鶴曾是花滑運動員,還因為自己在女兒出生時已是資深冰迷。「所有技術都懂」,張愛君悠然地回憶,臉上布滿自信的神情,她相信自己對花滑的通曉已達到國際裁判的水準。
張愛君和花滑的緣分是在「退休」後結下的。1998年,外企的工作令她覺得「干夠了」,那年她31歲。當初抱着定要成功的想法進了外企,張愛君想管項目、當女強人,但現實卻以一顆螺絲釘的角色回應她,每天做的無非是倒咖啡走紅毯,盯着天氣預報確認老闆的航班會遭遇幾號風球,更要命的是外企壓根不給她左右項目的機會。再到後來,張愛君發現外企裁員時整部門整部門地踢人,這使她對自己的處境更加疑慮。
當然也有快樂事,比如繁雜的工作使張愛君變瘦,她終於有自信像其他女人一樣穿起裙子,並「像麥當娜一樣」散發魅力。但這些快樂都太邊邊角角了,「如果找不到方向,我不可能待在外企,我一定要成功,」張愛君說,「我的人生是有限的。」
1993年,在釣魚台國賓館的一場宴會上,張愛君向一位美國老太太求解,「你能告訴我多少歲是一個女人最重要的年齡嗎?」
在那之後,張愛君辭了職,跟着周圍人玩花滑,滑行令她感到自由。同時,對成功的渴望仍在支配她,這次,張愛君想在圈子裡滑得出人頭地。那段時間,張愛君每天早上8點到冰場、晚上10點回家,大清早的冰場沒什麼人,保安站邊上給她鼓掌。她甚至為練習花滑做了流產,並如願在自學一年後,學會了五種一周跳。
她確信沒有自己幹不了的事,就連流產後走出手術室也踩着高跟鞋、昂首挺胸,意在證明即使自己一個人來,也足以應對。但是,一次摔傷將張愛君的認知猝然打碎——在練習燕式轉時,張愛君摔在了冰面上,右半邊臉近乎破相,她再也不敢上冰了。此後她開始全身心地整理花滑比賽錄像帶,研究選手動作、裁判評語,漸漸地成了一位民間花滑專家。
流產後,懷孕變得困難,做了兩次試管都失敗了,直到2006年,張愛君才等來自己的孩子,這年她38歲。後來,張愛君將38歲視作一生中最重要的年齡——這似乎應驗了那年美國老太太回答她的話,儘管不太完美:她那天告訴張愛君說,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年齡是39歲。
最初,張愛君以為懷的是男孩。她心想,男孩練花滑可就太容易了。和女孩相比,男孩的體能會在發育期獲得增長,更能控制身體變化。但2006年平安夜分娩時,迎接張愛君的是一個胖胖的、頭髮濃密的小女孩。
起先,她給妮妮取名「安怡冰」,她希望女兒喜歡滑冰。後來算命,說「冰」不好,太寒冷,張愛君便把女兒的名字改成現在的「安香怡」——之所以取「香」,是因為很多花滑女單的冠軍名字里有「香」,比如佐藤有香、荒川靜香。
對女兒花滑人生的謀篇從出生前就開始了。懷孕中,張愛君挺着大肚子剪輯花滑比賽音樂,丈夫安龍鶴看見了,覺得她是神經病,孩子沒出生剪什麼比賽音樂?妮妮出生後,為了避免日後遭到謊報年齡的質疑,張愛君早早就將妮妮的年齡公布在YouTube上——那種恥辱決不能發生在女兒身上。
還是新手媽媽的張愛君曾一度對失去女兒心懷恐懼。這是一個漂亮的孩子,「那月光一照,太好看了」。那段時間,張愛君每天都要想一遍,「這孩子死了我怎麼辦?」為體驗失獨父母的感覺,她每天都要看一遍叫作「星星港」的網站,邊看邊流淚。但這種情緒並未讓張愛君在女兒訓練上「心軟」,妮妮在經歷嬰兒期的體能訓練後,開始上冰了,這年她2歲半。不能再晚了,張愛君知道,如果走職業道路,3到6歲必須開始上冰,再晚將沒有冰感。
妮妮第一次上冰是在高碑店的浩泰冰場,之後,她開始像小蜜蜂一樣在北京各個冰場間輾轉,五彩城、大悅城、啟迪……但商場的冰場更像遊樂場,沒有誰會和妮妮一樣,為問鼎花滑賽場做準備。每到下午,商場裡就人山人海,張愛君和安龍鶴不得不帶妮妮轉戰他地;有時則是因為設備老舊,比如首體陳舊的制冷機一壞就壞十天半月,總無情收繳妮妮本就匱乏的訓練場。
如果實在沒冰練,張愛君就帶妮妮去蹭冰,她把禮物送給冰場清冰的大爺,拜託他趁老闆不在時偷偷給妮妮打開冰場的燈,大爺時常默默允諾。然而,有時也會因蹭冰被罵,「滾下去!」——這些不足以阻止張愛君,為了讓女兒有冰滑,張愛君可以「不擇手段」,破釜沉舟的勇氣早已成為她的一貫作風。
「我他媽早就是名女人了!」坐在妮妮的舞蹈課教室里,張愛君回憶妮妮幼時發生的事。到了五六歲,妮妮每天在冰場練八個小時,時間久了,常去冰場的人開始議論:「這小孩一天到晚不上學,天天在冰上練,長在冰上了!」他們覺得張愛君是個神經病,是混日子的,不然哪個母親會讓小孩不上學,天天在冰上滑來滑去?還有人奚落:「不用看了,過年就練廢了!」「安香怡你這麼練,三天,你就擔架抬走!」
張愛君一貫堅持着軍事訓練的強度,所以,當人們把嚴格要求孩子的母親稱作「虎媽」時,她覺得那不過是一頂雞湯的帽子,「教官」更配得上自己。「不是拿着炸彈炸她,讓她衝鋒,而是指揮官,有點兒像『欲練其功,必先自宮』,媽媽要先自宮才能推着這孩子往上走」。
這個冬天,張愛君總穿一條擁擁囊囊的黑色羽絨褲,這條足夠厚實的褲子幫她抵禦冰場的低溫。張愛君穿着它就像穿着作戰服。「我隨時變成吼,變成笑,變成暴,變成踢她,變成打她,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,是一個極限的性格訓練」。就像那天,張愛君把妮妮的合樂練習由三組增加到五組,原因是隔着冰面,她察覺到了女兒訓練時的不情願。
「練吧——五組!不想練也得練!」張愛君朝妮妮喊。儘管知道小孩並非機器,對往復循環的訓練也會顯露抗拒,但張愛君的做法是,若女兒對訓練安排不滿,那就強化這種訓練。「就是一個教官怎麼訓練新兵的腦子」,張愛君熟諳這種道理。妮妮嘴裡嘟囔,從冰場一邊滑到另一邊。張愛君發現了,昂起脖子又喊道:「你別廢話……老想偷懶……轉!轉他媽完了以後沒一次成的!」
更早之前,妮妮還是五六歲的小孩時,張愛君對此就已駕輕就熟,「我控制得非常好,」張愛君說,「她不可能哭鬧」,「訓練五個小時全在商場裡,每天晚上都獎勵她吃,買東西,買書,iPhone里App隨便下」,「這本來就是孩子的成長」,張愛君將之稱作「美國式的培養」。
管理妮妮令張愛君「入魔」,「恨不得你練到perfect,每個人都這樣,就跟審訊別人似的,越審訊越帶勁」。她將自己和胡適的母親馮順弟作比,「胡適多麼偉大的人,就是因為有偉大的媽媽」,「我打她是有社會責任的」。
現在,張愛君給妮妮立下要求:「摔得再狠也要把動作完成到指尖」。所謂「完成到指尖」,並不是調動肌肉讓指尖發力,而是要在花滑訓練中保持芭蕾的舞感。因此,在練習花滑動作的同時,妮妮需要時時提起足弓、繃緊腳腕,讓肢體動律經過膝蓋、髖關節、脊柱、後背、胳膊,最終抵達上肢最末端的指尖並將之延伸出去——這正是花樣滑冰不同於其他競技項目所在,它不是瞬間的爆發,而是跳躍、旋轉、步法多種動作的結合,它對運動員的形體、音樂舞蹈素養等等條項都提出了最苛刻的要求。
極致的訓練終於迎來了兌現的時刻。5歲時,妮妮第一次參加花滑比賽,並躍至6.5-7.5歲高級組別,獲得幼兒A組冠軍。這場北京市的花滑比賽便是妮妮的第一場奧運會,這以後,妮妮漸漸成為備受關注的小冰者,「全村的希望」、「陳露的接班人」,網友們在看完妮妮的花滑比賽後這麼說。
11歲時,妮妮開始在成年組的賽場上嶄露頭角,就在2019年,她收穫了三項賽事的成年組冠軍。但是,「成年組」意味着當一個11歲的孩子在冰面上演繹《lalaland》時,只能靠她的模仿能力,意味着她得在不停息的訓練中去掉身為孩子的那部分特質。
2014年,妮妮參加完北京市花滑錦標賽後,張愛君看到一條評論:安香怡只會做旋轉,除了轉什麼都沒有。」我他媽能服氣嗎?「張愛君說,「我5歲就會跳一周半,北京市冠軍,少年組甲組冠軍,全是冠軍,憑什麼呀?!」
晚上,張愛君趴在網上搜索這些評論,邊搜邊整理,越看越氣,她開始在訓練中加注500%的努力。曾有一天,妮妮練了十二個小時,「練到發燒為止,」張愛君說,「那時候我也瘋了,他們越說我越死勁練妮妮,因為我這人就是不服輸,就是輸不起」——「是一根筋輸不起」、「是死要面子「、「是要贏」。
要贏,這想法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支配張愛君。在這之前,張愛君對此毫無意識,她是班裡最差的學生,放學後總被留在教室補課。寫a、o、e,老師說「a」瘦得跟月亮似的。但比起其他孩子,張愛君更具成熟的「野心」。
她成長於軍隊大院,幼時的家庭生活於她很難稱得上溫暖,所以,在妮妮生日這天,面對擺着果盤和蛋糕的聚會氛圍時,張愛君對身旁的朋友說,「我們家不太會這個東西」。
在不長不短的童年裡,她一直在和自己敏感的神經交鋒。她擁有於她而言幾近透明的母親和父親,還擁有比自己大十多歲的哥哥姐姐。姐姐因父親偏袒張愛君而不滿,做飯時故意忽略張愛君的那份,張愛君既餓又氣,但又很明確地知道姐姐是「學霸」、「有本事的人」;而哥哥,一個浪蕩少年,抽煙喝酒,喜歡和哥們兒聚會,他總提拎張愛君的脖子。以上這些瑣碎的事,張愛君一向看得嚴肅,她仍清楚記得姐姐說過自己「醜八怪」。
另一邊,張愛君也羨慕哥哥和姐姐的生活,渴望像他們一樣,跳舞、辦活動、擁有舞台,但誰會正視一個小孩的需求?於是,出風頭的渴望被拒之門外,這使張愛君早早嘗到了孤獨的滋味,「為了出風頭我什麼都可以」,張愛君說。
愛出風頭的習慣是張愛君從母親身上學來的。母親愛追趕時髦、給家裡添置新物,從新款式的棉襖到新流行的書。1978年,母親被改革開放後興起的「外語熱」吸引,雖然後來一樣也沒學,但英語書、日語書、法語書都扎紮實實地摞在了家中的榆木方桌上。張愛君也跟着趕流行,憑着拼音和廣播,學會了用日語唱《我愛北京天安門》,「時髦得不得了」,時至今日,張愛君說起這些時仍顯得驕傲興奮。
2019年平安夜這天,在昌平區的一家養老院,張愛君站在走廊,傴下身子勸阻輪椅上想和自己回家的母親。屋外的雪天陰沉沉的,長桌上留着午飯餐盤留下的餘溫。已經92歲的母親,因為年邁,說出口的和聽入耳的都是一些模糊的詞句,因此,為了讓交流更清晰,張愛君不時把臉貼近母親耳邊。
幼時,張愛君很少和母親這般親近,母親熱衷事業,為奮鬥成北京市先進工作者和站上天安門觀禮台而努力。她每天清晨5點出門,乘有軌電車上班,夜晚回家時,張愛君已經入睡。不過,昔日這些並沒有妨礙張愛君對母親的了解,她知道母親之所以想和自己回家,是因為她不需要養老院的那種好,她需要一直自己做主地活着。
唐山大地震那年,夏天,床在凌晨時分突然搖晃,母親衝進房間,抱起張愛君就跑。「我媽真是個英雄啊」,張愛君在回憶中發出讚嘆。正是這件事讓她意識到,「她仍然是個好母親」。
但在她的記憶里,童年裡陽光燦爛的日子都是父親給的:帶她騎車、游泳、去麥地,把她馱在身子上繞着屋子爬,開家長會時,坐在教室里的人也總是父親。
有些事情已經很久遠了,但張愛君明白無誤地記得,當年她令父親觸犯交通規則、令父親被老師喊去訓話時,她內心的愧疚。
因為忍受不了全托班對自己的限制,那年的冬天,張愛君拿着從父親桌上偷來的大團結和自己攢的一盒鋼鏰,跟另一個女孩跑到紫竹院公園,玩滑梯,盪鞦韆,一天過去,麻煩來了。張愛君不僅被父親揍了一頓,更被老師喝令,從大班蹲到了中班。從此這種慚愧與不服氣進入她的身體。
直到三年級,張愛君才被「喚醒」。起因是一篇作文,這篇由張愛君半抄半寫拼湊而成的「傑作」被老師當作範文,當眾表揚。這便是她與「贏」的首次會面:原來當第一這麼好!當父親因自己的成績而成為家長會上的第一名時,張愛君意識到了,要考第一、當學霸,為父親帶來榮譽。她不允許榮譽下墜,後來沒考到第一時,張愛君就偷偷抽自己嘴巴,現在,張愛君也這麼理解女兒:
「看到我哭,看到我生氣、被外頭人罵,妮妮都特難受,她想往死里給我爭榮譽,這就是小孩對父母的心情。」
北京體育大學的籃球館裡,球撞擊地面發出嘣嘣聲。在靠窗那邊的絨白地毯上,一群小姑娘在練習藝術體操。妮妮是其中之一,正挨着地毯邊沿壓腿。張愛君站在一旁,給妮妮別頭髮。可能別得太緊,妮妮咧嘴喊疼。「裝什麼,哪那麼多戲,張愛君笑着說,「這就是另一個我。」隨後,她輕輕唱了起來:長大後——我就成了你——
在一次訓練中,曾有位母親向冰場老闆舉報張愛君「虐童」,原因是她在公共場所打罵孩子,擾亂公共秩序。
直到現在,張愛君在妮妮的舞蹈課教室想起這件事時,仍然神情激動。「那是小case。」妮妮在旁邊說。「你是小case,那他媽我特生氣你知道嗎?」張愛君說,她坐在一排靠牆的軟椅上,難以把心情從「被舉報」的氛圍里拔除,「像我們這種後媽,都是被人告的」。
對於妮妮的訓練,張愛君為之匹配了「自殺式訓練」法。運動員穩定的賽場表現,全賴肌肉記憶,但肌肉記憶的形成毫無捷徑可取,只能靠枯燥乏味、無限逼近極限的訓練,「就是往死里跳,」張愛君說,「每天一定要追求一個極限,這就是她(妮妮)的本職。」她時時觀察妮妮訓練的臨界點,包括體能狀況、休息時間。這過程常需要醫生跟進,及時處理訓練中的小傷患。
「就是拔苗,一種科學的拔苗,」張愛君說,「因為運動員就是要爭取成績。」但也有失控的時候。2018年10月,張愛君帶着妮妮練「高級三三」,這是花樣滑冰的一種高難度連跳動作。那天從下午到晚上,妮妮跳了三百多個,後來因為腿疼返回家中。當晚,醫生給出診斷:腓骨異常。
那次傷患發生在右腿——右腿之於花滑運動員如雙足之於飛鳥,因為所有跳躍都是右腿落冰。這令曾是花滑運動員的父親安龍鶴擔心,他仍記得在退役前的那場比賽中,來自右腿的傷痛如何給了自己消極的暗示。現在,傷病不時出現在妮妮身上。「腳踝三天兩頭出問題,一點都不出問題她媽就不高興了,(覺得)沒練夠。她媽媽就是出了傷病了就該休息了,不受傷那就得練。」父親安龍鶴說。
「你要贏,你必須是我這種媽,不服輸的媽,普通的媽不行,肯定不行。」張愛君說。
即使在最害怕失去女兒的那段時間,張愛君也意識到這種愛是一種「小愛」:胖胖的嫩臉蛋誰不想摸?每個人都喜歡可愛的嬰兒——但她決不能被「小愛」占據,張愛君把自己從與失獨父母的共情中剝離,並在日後訓練時,去掉了作為母親的那種心疼。「你丟炸彈、上戰場,你害怕嗎?但是你要不要幹下去?去掉心疼就是你的課題,沒有什麼去不掉的」。
那次,連跳三百個「高級三三後」,為了恢復,妮妮暫停了練了三個多月的3A—— 一種相同周數下頂級難度的跳躍動作,被稱作「領獎台必備」。但對運動員來說,恢復傷病的過程會影響肌肉記憶,之前的艱難練習很可能被「一筆勾銷」。花滑運動員如果三天不上冰,可能連跳躍都不會做了,女孩尤其如此。後來,妮妮恢復了兩個多月後,不得不從頭練起。
安龍鶴有時提醒張愛君,要注意防止傷病,但提醒時常失效。不僅是因為張愛君對妮妮的訓練占據主導,還因為安龍鶴結束泰國的工作回國時,妮妮已經5歲多,「她的思想是跟着她媽媽走的。」安龍鶴說。妮妮幼時訓練,安龍鶴擔心練廢,但張愛君不認可,她告訴妮妮,「咱們非得滑一個全國冠軍給他看!」妮妮也模仿張愛君,沖父親說:「我媽說我不會廢的,我媽說的什麼都對!」
所有人當中,唯一能對張愛君訓練計劃提出異議的人是丈夫安龍鶴,但當他擔心、發牢騷時,張愛君常常只是沉默。
有幾次,在俱樂部訓練時安龍鶴差點將拳頭對準張愛君。一天,張愛君在屋裡吼妮妮,安龍鶴聽到了,以為她在打女兒,便也吼着衝進屋裡。神經病,他這樣罵着。但推開門後,他看到張愛君正在抽自己嘴巴,把腦袋往牆上撞,妮妮也跟着張愛君做同樣的動作。張愛君常以這種方式威脅妮妮,以按捺她在訓練中的急躁,她期望女兒能平和地訓練,否則將陷入最容易受傷的危險情境。但對於這天的事,安龍鶴想不起來了,「有些事情記着太累了,總記着心裡難受,就忘掉,就算了。」安龍鶴說。
當妮妮如小蜜蜂般在冰面旋轉時,張愛君為自己和安龍鶴找到了「各司其職」的方式——她讓家庭像公司般運作着。「你不能像家裡那樣運作,那你就累死了,像公司一樣運作才能產生尊重、最高效率」。
在這間「公司」,「CEO」張愛君制訂的行事準則是「老娘說了算」,「奪權,就跟宮斗一樣,男人是不服女人的,男人都是巨嬰,他不會跟你妥協,你只有拿權力壓着他。」而她和安龍鶴的相處方式,則是協作和禁言。
協作是張愛君和安龍鶴在妮妮的訓練上相互配合。安龍鶴負責教技術動作,張愛君則帶女兒學舞蹈;禁言是兩人現在很少對話,主要通過微信打字溝通,「通過打字才能互相尊重,(因為)婚姻關係太近了就容易互不尊重,所以必須閉嘴,拉開距離不理他,才能得到祥和。」張愛君說。
其實在更早之前,領結婚證的時候,張愛君就已決定「脫離」安龍鶴,「因為我只有脫離他,才能塑造世界級的」,「婚姻在我這兒就是公司,共同生活」。
張愛君相信,發生在自己和安龍鶴之間的爭吵會使妮妮獲得免疫力,「慢慢覺得男人沒有意思,婚姻也沒勁,這就是成長,」張愛君說,「世界哪有那麼簡單啊,很殘酷的,我是很悲觀的……(對他)愛得深,(那)他一離開你就得死去活來。」
你會很想知道張愛君的心裡是否也有裂縫,是否後悔過、搖擺過?你問很多問題,但她總能在自己的世界中說服你。「在外人看來我們特別崩潰,但這是我們人生最好的體驗。」張愛君說,「我被說成是後媽,(但)真相是不一樣的,我這個更接近於(人生的)真相。」在她心中,那真相事關一個人自我成就的本分,自然也包含了不得不付出的代價。
那天妮妮練習合樂,張愛君倚着圍欄,沿着探向冰場的脖頸,她把清亮有力的喊聲拋向妮妮:「你別廢話,老天讓你多合幾遍!」妮妮站在對面,以一種自言自語的口氣小聲反駁,「能不能別老天老天的」。
「我需要這樣的土壤活着。」張愛君說。她信佛, 訓練時,習慣用「渡劫」「老天」「修行」這些詞向妮妮解釋她所面對的事,「要一邊練一邊講人生」。當妮妮在冰場上摔倒時,張愛君會這麼解釋:
「老天安排就是讓你渡劫的,就是不讓你成,讓你多練,你要感謝老天!……你要真成了比賽就摔了,這就是修行……你的劫數並不因為你的痛苦而減少,那山,不會因為你刻苦就低了,你知道嗎?」
當她在妮妮訓練中踢東西,顯得躁鬱時,張愛君說,那其實是在幫助妮妮,「我們是沒有媽媽孩子這種階層概念,我們是靈魂的相互成就。」
「我作為一個媽媽,我走過了所有女人所走過的路,只不過更加極限,更加極端,更加焦慮,當有了這一切之後,我所學會的就是我的劫不會停止。藝術是通過缺陷來打磨的,藝術之花,你的劫有多深,你的花就有多美,就是一朵蓮花,它會長在大糞上,它會長在刀尖上,我們就是在大糞里、在刀尖上修行,不但要扛疼,還要扛臭。」
現在,從張愛君母親的積蓄到妮妮的獎金,三代人的財富都在供養花滑。張愛君懂得「花錢的藝術」:當這個家庭每年將60萬用在妮妮身上時, 她為自己買20塊一打的襪子、或者廉價的內衣內褲。妮妮每個月的按摩理療費是七千到一萬五,還有高品質的食物,新鮮的果汁、地中海的橄欖油、椰子油等等。也因此,在聽到別人說妮妮練得殘酷時, 張愛君會說,「根本不是,特別的幸福」。
2019年12月,在深圳萬象城的冰場邊,張愛君被一群家長圍在中間。這些家長剛看完妮妮的表演,他們用崇拜的目光注視張愛君,並好奇她對妮妮的培養之道,「咱們快聽聽大師講課。」一個家長說。張愛君聽了急忙糾正「:什麼大師,你別給我亂安排名字,我就只有一些教訓給你們聽,沒有什麼課給你們講。」
沒多久,人群里又傳出問話「:安香怡自己喜歡(花滑),有成就感是嗎?」
「和她自己喜歡一點關係都沒有,」張愛君說, 「無論孩子選擇、家長選擇,只要她在這個行業做出成績來,她就會自己喜歡。有句話是這麼說的:nothing is fun, until you good at it,什麼事情都不是有趣的,直到你擅長它。」家長們神情崇拜,點着頭。
當別人對妮妮的成績讚不絕口,感嘆張愛君是個成功的媽媽時,只有張愛君心裡知道,他們挑了條多麼冒險的路。妮妮有可能練廢,張愛君知道那是很可能發生的事,她實際上怕得要死——妮妮不上學,沒有應試教育的路可走,她們賭了花滑, 但尚未取得大成績,必須滑下去,滑出成績,不成功便成仁。
妮妮必得如此,張愛君更甚。「唐僧取經,妮妮並不是唐僧,唐僧是我。」張愛君說,「我並不想當唐僧,可是上天就是讓我干唐僧,那我怎麼辦?」
如果一切順利——最順利的那種順利——張愛君會像金妍兒的母親那樣,為女兒籌辦國際級花滑秀。「希望我也有那一天。」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,妮妮至少得拿一次世界冠軍,為維持冠軍熱度,還需要在世界A級賽場上待夠起碼兩個賽季。
冠軍、金牌,這些東西就像人類社會的舊容器,在盛放人們的各種需求時總表現得適宜。雖然在面向外界時,張愛君像很多運動員一樣,說不在乎金銀銅牌,但她知道,這就是一個爭奪第一的行業,「當運動員得銀牌我沒感覺。」張愛君的聲音在嗓子裡繞了一圈。妮妮坐在一旁,細長的眼睛看向母親,窄小而精緻的臉上,眼神又淡又遠。
「至少是第一次比賽,第二次比賽我就算了。」 張愛君說。
「但你還得拿。」妮妮接話。
「當然了,我一定要拿一次。」張愛君說。
「但你拿完一次覺得自己還得拿,第三次你也還得拿。」妮妮又說。
「隨便你怎麼想。」張愛君說。「因為有錢吶。」妮妮說。
「你呀跟我一樣,這就是我的孩子,別的都能沒有,不能沒錢,你終於說出了我的痛點。」張愛君笑着,把臉轉向身旁的朋友。
生日這天,妮妮趴在休息室的一排軟凳上和一個小姑娘聊天,倆人捂嘴嬉笑,像在分享秘密。過了一會兒,妮妮站起身來,給身旁的小姑娘模仿塗了口紅的女人怎麼吃飯,隨後,她們發現了彼此在塗口紅這件事上的共識:都不喜歡。這天,妮妮和小姑娘閒聊了約25分鐘,這在她的生活里是少見的。張愛君將妮妮視作一個不需要同齡夥伴的孩子,因為真正的精英都是孤獨的,「孤獨是作為一個領軍人物的必需的童年,」張愛君說,「靈魂永遠都是孤獨的。」她認為妮妮的朋友要比妮妮大至少20歲。「每個人都要把自己送進階層里去……你做優秀的運動員,你要是成為優秀的人,你不能跟同齡人混在一起,只能是比你更大的,有經驗的」。
在張愛君眼裡,所謂孩提時代的同齡夥伴,大多都是「廢物」,只會耽誤時間——「妮妮是為保護動物和升國旗而奮鬥,跟閨蜜會產生幸福嗎?」很難確切解釋張愛君的理念從何而來,但她確信女兒需要孤獨。妮妮也的確是這麼長大的,從小到大,圍在她身邊的人是張愛君、安龍鶴,以及前綴着各種姓氏的老師、教練,還有貓。
當別的孩子在旁邊對着鏡子玩自拍時,張愛君不准妮妮加入其中,雖然她並未言聲,但妮妮仿佛已全然領會,她只是抬頭往那邊看,並未湊近。沒人知道妮妮那時在想什麼。張愛君覺得,她培養妮妮,所以妮妮和自己成了同一種人。
不過,妮妮也沒有交朋友的時間,訓練和休息占據了她的生活。張愛君很少把時間耗費在其他地方,她不僅是妮妮的教官,還是她的保姆、司機、經紀人,「所有一切的一切」。這些工作已持續近十三年。
休息會令張愛君內疚,她和妮妮每個月的休息上限是兩到三天。通常,結束陸地和冰上訓練後, 一天已過去五個小時。張愛君這時會開車帶妮妮趕到舞蹈、藝術體操的訓練場,再繼續三至七小時的訓練。而往返於其間的路程加起來幾乎有100公里。上完這些課,如果時間允許,她們有時會去商場吃晚飯、看電影——看電影時要去最貴的影廳,張愛君的意思是,「只有接觸過最好的之後,才不會繼續嚮往、貪婪。」
晚上回家後,妮妮需要學習文化課,也需要壓腿、壓胯、踩腳背。不過訓練緊張時,文化課會被擠掉,「太累了,唯一能犧牲的就是文化課」。張愛君時不時地把妮妮的花滑、舞蹈訓練以及擼貓、製作美食的片段拍成小視頻發到網上,告訴人們,這個孩子不是除了滑冰什麼也不會。
作為公眾形象營造計劃的一部分,張愛君也會培養妮妮的說話風格,她摸着胸脯給妮妮示範如何輕輕地說「怎麼了」,還有禮貌的儀態,「說謝謝了嗎?說謝謝時要彎腰鞠躬。」
這天走出滑冰場的休息室時,張愛君告訴女兒,不要抱怨沒有自己的時間,要為了國家,要行大愛。妮妮應聲聽着,默默地。
妮妮很多時候都是「默默地」,默默地坐在汽車後座上舉着手機刷抖音上的美食短視頻;默默地從桌席上撤下躺到後排的椅子上休息;默默地拉着行李箱分辨指示牌走在機場大廳。她很少反 駁,也很少提出需要,她似乎自己就可以搞定所有事,總顯得利落而迅速。對於別人基於妮妮是孩子而想提供的幫助,張愛君總是先於妮妮提出拒絕, 比如幫妮妮從比她更高的行李架上取下行李箱, 「讓她自己來」。
對於別人的問話,妮妮也很少表現出繼續聊下去的神情,她只是禮貌性地回答,微笑着,然後沉默。你知道那每每都很整齊的微笑不是在表達私人情感。但這些令常人眼睛驚異的12歲女孩的成熟氣質在張愛君眼裡是稀鬆平常之事,「妮妮的心理年齡早就三十多歲了」。
張愛君有時也會表露出人意料的興奮。這天結束藝體課後,她們驅車前往電影院。坐在駕駛座上,張愛君逗妮妮,「妮妮,你是我奶奶,你說是嗎,妮妮?」她側身轉過,把手放在坐在後排的妮妮的膝蓋上,妮妮的左手也搭了上去,張愛君為此開心, 她以輕快的口氣告訴旁邊的人「:你看她也把手搭上來了。」
訓練這天,張愛君站在滑冰場的休息室,當她轉身看到正和小夥伴閒聊的妮妮時,她以膝跳反射的速度說道「:臥槽,發育期了!」
張愛君無法避免對女兒正在到來的發育期的恐懼。「你不知道以後是什麼樣的,這是很難戰勝的,因為你只有一個孩子,也沒上學,也沒有什麼別的路可走」。
但妮妮的發育期就在眼前。她已經長得像個大姑娘,連海拉爾那場比賽的解說員都說,妮妮在半年內至少高了半個頭。時間是緊迫的,正如張愛君曾向一位母親建議:「你一定要(讓孩子)在身體變沉之前趕快完成三周跳,你就得搶你知道嗎?」 「身體變沉」是女孩在發育期的變化,在花樣滑冰界,發育期一向是女孩們要面臨的嚴峻考驗, 很多青年組的種子選手因之被擋在成年組賽事之外,儘管瑪麗亞·布特爾斯卡婭曾在27歲時登上過世錦賽冠軍的領獎台,但更常見的情況是,女孩十幾歲時在賽場上嶄露頭角,此後卻因為各式原因卡在發育關,從此銷聲匿跡於花滑賽場。張愛君熟知這些,她明白女孩要在進入發育期之前抓緊攻破技術難度,最好在8到13歲之間完成所有高難度動作。這是在和時間賽跑。
父親安龍鶴的預期是在2020年8月,妮妮可以在賽場上完成3A,「越早越好」。但在最近的訓練中,安龍鶴感覺到了女兒的恐懼:起跳後,本該在空中旋轉三周半,可妮妮總不時放棄,「只是比畫了一下就落冰了」。安龍鶴理解這種恐懼,和其他跳躍相比,跳3A時,運動員在空中的旋轉轉速更快, 使用的力量也更強,在這種情況下,如果出現失誤, 運動員會摔得更重。但別無他法,安龍鶴必須要求女兒完成動作。
除了眼下的技術關、發育關,太多事情擋在前面,等走到盡頭,還有一個難以企及的強大對手。但張愛君不得不如此,妮妮不得不如此,安龍鶴也是,他們得去奪回一些匹配得上他們野心和犧牲的東西。
平常的一天結束了,天黑了下來,張愛君要去往馬路對面。在對面那座灰色的樓里,妮妮正在上舞蹈課。這時,一輛汽車朝她駛來,帶着夜色中模糊的輪廓,汽車沒有鳴笛,只顧往前。張愛君趕忙後退,「就像這些車永遠都不看着你,這個社會就是這麼沒禮貌」。
在張愛君將之稱作「大糞」的社會裡,她和妮妮在為開出一朵潔白的花而努力,「我們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,就是要完成這個過程,哪怕是抓住一把刀子,我們也要握住機會,就算人生是夢一場,夢中的所謂這些修行不也很美好嗎?」張愛君已經走到樓下,「夢裡也是很有意義的」,她接着說。
夜色已將張愛君包裹。冷風吹起,明亮的燈盞從街的兩邊沿向天的四方,凝滯許久的東西仿佛瞬間化開了。此刻,在張愛君別在腦後的馬尾上,頭髮隨風漂浮,它們仿佛生來就是那樣,飄蕩着,在夜裡隱現出一個風塵僕僕的背影。
C o n t r i b u t o r s
執行:Diana、Kyra
新媒體責任編輯:Neil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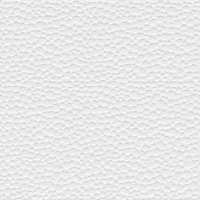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評論列表
文章我看過,感覺說的挺對的,有問題的話可以多去看看
被拉黑了,還有希望麼?
被拉黑了,還有希望麼?